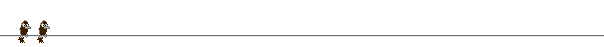 饥饿
饥饿
公子小白
灰认识川是在一个洒满阳光的午后,太阳亮得可以看清对方脸上的任何一处
细节,他有老人斑了,灰坐下来跟他喝下午茶的时候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在取点心的时候,不经意地碰了一下她放在桌面上的手,灰攸的感到一种
温暖的湿度,她下意识地抬头望向他,四目相投处,灰象猛的被人剥光衣
服,川一下子笑了,她面上的那份茫茫然又使他忆起他和她的第一次相遇,
小小的她蜷缩在吧台的一角,四周混乱和嘈杂似乎都与她毫不相关。
实际上她算不上美,瘦瘦的肩,窄窄的骨盆,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暴力片中被
人一拳灌到墙上,然后便会反弹回来的那种无可奈何身不由已的瘦,她就蜷
缩在那儿,一个人闷闷的喝啤酒。眼睛直视着舞台上疯狂至抽搐的DJ的挪臂
甩胯。川那天正闷,纯属好奇的走过去,轻拍了下她的肩膀。她并没有那种
初识陌生人时的慌乱。眼睛只是从舞台上的五彩缤纷转向他,一样的空无一
物,她笑了一下,似在挑逗,他那时发现她的皮肤出奇的白,好象是长期没
有经过日光照射的,泛着冷冷的光,象暗室里的一颗琥珀。
他请她喝鸡尾酒,她没有向他道谢,端起酒喝过一口,好喝。她已有些微
醉,象只午后的猫,软软的从身体到声音,犯着一种生命的腻。你蛮有钱
吧?她从开始就直切主题。这很重要吗?他望着她,一种莫名的心疼。她神
经质的玩着杯子,很天真的笑,我喜欢有钱人。她就这样赤裸裸的呈现在他
面前。
她不是鸡,鸡出卖肉体;而她,出卖灵魂。
川自己有个小公司,颇有资产。太太死后,他将一双儿女送出国,便开始了
一个人的独居生活。他喜欢这种状态,维持了二十年,他一个人,在一套偌
大的房子里,连保姆都不请一个。
灰第一次到他家里去,便诧异于这里竟住的是鳏夫。客厅里奢侈的壁炉,一
贯到底的落地窗,四角里垂涎欲滴的长青植物,全被中央铺的镂着拜占庭式
米色花纹的大红羊毛地毯抢尽了风头。黯然失色着,形同虚设。那东西肆无
忌惮的向来客袒露着它干净而温暖的身体。使人联想到床,但这又不是卧
室。
整个房间都弥漫着一种怪诞的一尘不染。
我喜欢干净,干净的枕头,干净的床,干净的房间,干净的女人,他为她斟
了杯法式白兰地,竟也是纯净的,毫无杂质。这些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乐趣。
他在她啜饮时,吻了她的手。他的嘴唇湿而冷,使她联想到蜥蜴。
我们在哪儿做爱?灰开始心烦意乱,酒流进胃里,使她的小腹灼热。
川不自禁的笑了,他引她进卧室,关上门,打开壁橱,琳琅满目的各色女人
内衣。
你喜欢哪件,它们都是新的。
她换衣时,他去烧洗澡水。她出来立在浴室门口,他正弯腰用手试水温,鬓
角的头发垂下来,有几缕在暧昧的灯下闪着银光。他是见不得光的,她不快
的想着,他已抬头,正望见她,她挑了件蕾丝的长款睡衣,黑缎包裹住她孱
弱的身体,胸前隐隐约约的一点,恰如春梦了无痕迹。
他怜爱地低下头,吻她的额头,嘴唇,脖颈……她靠在冰冷的水磨石墙壁
上,闭了眼睛,一寸一寸的领受他给予她的潮湿,在无边的欲望里一阵阵昏
迷。他终于暂时的放了她,去换睡衣。
她让自己瞬间赤裸,慢慢的在水中沉没。感觉一池清波慢慢被欲望浑浊。她
忽然想起菊苑,想起大学。水气氤氲里,她看到她和它慢慢地萎谢死去,被
抛进污秽的河里。
她感觉到一双手在她的背部轻轻的抚摸。是它,它来了。
一夜听外面的雨声,迷迷糊糊地天便亮了,菊苑去水房洗了脸,穿上素净的
校服,呆坐在床沿上,有一种虚脱的感觉。直恶心。
昨天她又在学校那大大的,破败不堪,永远烟雾弥漫的浴室里莫名的晕倒
了,脸变成灰白色,身体瘫软象一具尸体躺在水淋淋的水磨石地上,令人联
想到奥斯威辛的毒气室,想到赤裸着走向死亡的犹太人。她被同学扶出来,
坐在休息室的长椅上,瑟缩着,长发湿淋淋地披散下来,遮住了她的大半张
脸,只能见到她白森森的牙齿紧紧地咬着失血的下嘴唇,似不会说话,那个
同学问她还好吧,她努力的点点头,出于礼貌勉强地向人家微笑一下。
阳光依然苍白着。菊苑下楼,走到男寝门口,来来往往着的都是拿着脸盆,
嘴上沾着牙膏沫的男生,有个下级的学弟一直在暗恋她的,看她立在走廊
上,便接水,关门,倒水,从她身边频繁的走过。低着头,青青的下颏,细
细长长的腿,没有声音的爱着她。
“什么事?”那门只裂开一条缝儿。
“找小柏……”
“小柏,有人找。”那开门的不耐烦的喊。
小柏正歪在床头看书,看到她也没什么反应。只说:“有事?”
透着那种晦涩的不热情。
满世界一片尴尬。
“图书馆楼下我等你,有话说。”
小柏只说:“可以,可我还没吃饭,晚点儿吧。”她看了他一眼,喉咙瞬间
失了血,再也无法发声。
等到走出来,径直坐在平时坐的木椅上,夏天里阳光毒得早,她就那样执拗
地坐在阳光里,苍白着一张脸,手指因洁癖洗得透明的白,无聊的搭在靠背
上,她也不确定自己是否会一直等到他来,心底凉凉的,身子发飘。
同系的一个女生踏着木屐,远远的向她挥手,青春得似露水。
人慢慢的多起来,来去匆匆,行走于不同方向,无数个交叉点,只有她在静
止着,菊苑无聊中想。小柏远远地走过来,胳臂夹着书,手抄在裤袋里,菊
苑向他招手,不自禁地微笑。他把书放在两人中间,说:
“有事吗?”
这个开场白让她始料不及,惊愕的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他是不会给她矜持的
余地的,连客套也给注销了。
四下里沉寂下来,也鲜有人走过,远处网球场上几个人在打球,一来一往的
“嘭嘭”的挥拍击球声,许多事她现在才想清楚,都是些无聊的过渡,除了
过渡,一无所有。
这时她还能笑出来,隐隐的有一种为什么献身了的感觉,她还那样远眺着,
不经意地说:
“我想回老家……”她又把球打回去。
“为什么?”球嘭的一声又弹回来,她不得不陈述理由,无外乎父母年岁老
大,自己毕业后又远离家乡,诸多的放不下……她的灵魂走出来,远远地看
着她,看着她在无休止的絮絮叨叨,心一阵阵下沉,没有了底。
说完闭了口,直视他。从此她一无所有,连身体都已不存在,只剩下那座位
上的一口气。小柏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思忖,又好象在发呆:
”别走了,留在校园里。跟同学们在一起……毕竟离毕业不远了……”他毫
发不乱的讲着。余下的话,化成一只蚊子,嗡嗡嘤嘤的绕着她飞。
她无力的摇着头,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然后再不想说一句话,阳光那么苍
白,她想。
川的寓所里的房间很多,却都是一贯到底的落地窗,他喜欢用真丝作窗缦,
客厅里的是乳白色的,书房里的是淡蓝色,卧室里的是深紫色……夜色被其
包裹着,象一群穿着华贵的裸女。氤氤着一层半遮半掩的欲望。他习惯于下
厨给她做各色的甜点,这样才能拴住女孩子的心,他说。
他狡猾地爱她,但她不承认。
她心情好时会陪在他身旁,偶尔开个玩笑,时常川会被逗得笑起来,象个孩
子样的。灰茫然的等待川笑尽,不屑中竟带着一点她自己都不相信的怜悯,
对他的怜悯。他的眼睛里闪着天真的光,只是他太老了,一笑起来,牵动那
么多的皱纹,悲惨不悲惨,分不开了,每念及此,灰的脸上总会泛起与她年
龄不符的冷笑。
这时菊苑便会趴下来,逼视着她的眼睛,灰,你快乐吗?你真的快乐吗?
快乐又怎样,不快乐又怎样。灰一脸的无所谓。
若你真的快乐,一切便都值得。菊苑翻转身躺着,叹一口气。
灰靠过来,抱住她,象抱紧自己,菊苑,我爱你,我爱你,菊苑。她喃喃的
说,夜再没有尽头。
菊苑长长的睫毛垂下,遮掩住不为人知的心事。她时常坐在宿舍的窗台上抱
着双膝,将瘦削的脸埋在里面,不时的眺望街景,房门敞开着,灰趿着拖鞋
在楼道里唱郑钧的《我的爱赤裸裸》,很苍凉的声音,她们都很寂寞。
傍晚残阳如处女之血,洒满天际。
菊苑,楼下有人喊。是小柏。菊苑在床上翻了个身,没言语。灰便隔着窗台
望出去,小柏站在树影里,向她微笑,笑影婆娑着,灰转头对里面说,真不
见,这么帅气的小伙子。
她不在了,去世了。灰扔下一句,把窗子随手啪的关上。
菊苑抬手开书架上的录音机,频繁的旋转调台,里面传出七腥八素的各色音
乐,被人为的斩断着,肢解着,抽搐着,顽强的歌唱着。
灰实在呆不下去,便去找川。她一脚踏进夜色里,那才是她的世界,黑暗,
所以适合逃亡。
门启处,川和那间硕大的房间便显露在她的视野里。川站在那里向她微笑,
很温暖,带着一种家的气息。你好吗。他说。她忽然有一种冲动,想去拥抱
他,他在她的心中从未有过如此熟络和亲切。她抗拒着这种莫名的冲动。川
拉她进去,关了门。
客厅里电视开着,在播一场晚会。
你在做什么?
等你……
灰自嘲似的笑笑。你这话听起来象个独守闺房的怨妇。
你是我唯一的客人。
不可能。
当然早上还来了一位……
谁?
修瓦斯的。
你为什么不工作。灰顺手用扔在沙发上的遥控器换了个频道。国际新闻,布
什正在叫嚣,战争一触即发。
后面的手伸过来,搂住她。她默默的感受他因胡须而微刺的脸颊。年青时我
不得不为社会当牛做马,现在我只要爱,爱你。她不回答。
他递给她一张信用卡,礼物。他说。她没有犹豫的接过来,收好。他为此有
些讪讪的。没有人在乎形式。
我去洗澡。她总是直奔主题。除了性,我们再没有什么可谈的吗。他在她身
后说。对,我是动物,只会性交,不会思考。她拉开浴室的门,走进去。
那个晚上,他们在客厅中央的那块镂着拜占庭式米色花纹的大红羊毛地毯上
交媾,她被他弄得很痛,他似乎在报复。她没说什么,在他的孤独中达到了
高潮。
菊苑一个人走在下晚自修的路上,灯火阑珊处,一记颀长而寂寥的影子。
他拉住她的手时,她只是觉得很陌生,对他陌生,对自己心底的爱陌生。她
怀疑着自己,是不是禁闭的太久了,她已经不习惯这种表示亲近的形式。他
们没提上次的话题,没有人敢干提起,敢干面对,一路说着无关痛痒的话,
每个人都很自然,当把爱放一边时,他们是最和谐的朋友。他曾经这样鉴定
过他和她的关系。
他要的是她红颜知己的友谊,她给他爱情,他知道,然后他接受,暧昧的接
受,却不回答。这是他的个人风格,什么东西他都可以打折似的妥协接受,
连爱也是。
她被他握着,心里幸福着,被自己欺骗着,忐忑着,失落着,压抑着,不满
着,无奈着。她吃着他施舍给她的残羹冷炙,她矜持,她有她的骄傲。是
爱,是爱让她沦为沿街乞讨的乞丐。
走在风里,他说,也许你不知道,我很寂寞,寂寞得象风中的一棵树。她想
起有关他的一切,有关于他的招风引蝶,有关于他的朝秦暮楚。他是风中的
一棵树,一棵飘摇的树,在路的尽头开满了花。
风吹过她的鬓角,她笑笑,笑得象爱中的一道伤痕。灰的身影在她眼前跳跃
着,她突然想,自己也不过如此。
我是有一点喜欢你的。
那也很好。她从容的回答道。
她甘愿落入他设好的圈套,堕入,然后万劫不复。你知道吗,你会爱我的,
在以后。她竟有些固执的说出这句话,象死前的最后一次挣扎。
在路的尽头,他吻了她,然后他们告别,各自走各自的路,她停下来看他的
背影,她为什么爱他,至今已记不得了,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刻,究竟为
了什么。只是觉得他们曾经认识,或者前生,或者来世,他们遇到了,便再
也拖不了干系。只是他已不记得她了,他已经爱到迷乱,爱到没有时间去细
细打量,她的鬓发,她的眉眼,她心底为他一个人盛开的花园。
灰病着,躺在川的家里的大床上,无声无息的,象一只发焉的猫,她的意识
时清醒,时糊涂,只是感觉有一双温热而干枯的手不时地抚摸她的脸颊和额
头。
她去找柏,那个阴柔的如地狱之花般的男孩子,他有一句很颓废的名言,我
很寂寞,寂寞得象风中的一棵树。她因鄙夷而亢奋。她约他出来,在一处干
净的房间,午后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很慵懒的爬进来。
我们为什么来这里?他有些拘谨似的惊奇。
你不明白吗?她拉他的手。他坐下来,她斜睨着他,他会害怕或厌恶吗?她
不无好奇的想。
不明白。他的手冰冷。神情竟有些僵硬。
她突然轻笑了一声,你怕了吗?怕我会吃掉你。
他不作声,凝视着她。退却着,不敢招架她的咄咄逼人。
为什么?
我要得到你。她盯视他,象盯着一件猎物。
我不会让你负责的,我永远都不会要你什么,哪怕是你的一句承诺。她望着
这个一向清高自傲的男人,她至今也无法预料到他会有怎样的决定。是给她
一记响亮的耳光,;抑或是鄙视的不置一词的弃她而去。
她踌躇着,肉体却兴奋着,她象在等待死亡宣判。然后她看到那双如河中星
斗般阴柔的眼睛俯下来,她的世界一片黑暗。
有些人生来就是为了活的,有些人生来就是为了爱的。她听到他用加缪书中
的一句话来解释他和她之间刚刚发生的这一切。他的爱冠冕堂皇,充满了无
数浪漫的理由。而这一切都与他和她之间刚刚发生的动物性的一幕形成太鲜
明的反差,象一只丧家之犬被贴上灵魂的标签在人声鼎沸的超市里公开拍
卖。
人死去肉体便会随之腐烂吗?她突然问。
他疑惑的望着她,望着这个方才淫荡无比的女子。我们在做爱,为什么想到
死。
你没有闻到一股死亡的气息吗?这房子里有一股死尸的气味,弥漫着整个房
间。
他随着她枯瘦的手指望向空中。然后他翻了个身,骂道,神经病。她爆笑
着,浑身都因笑声而震颤。
梦里,她奔跑着,饥饿着,因饥饿而奔跑,因奔跑而更加饥饿。满世界横陈
着死尸,仰着头的,没有内脏的,肢解的,蜷缩成一只虾的形状的,两个人
搂抱着交欢的。她到处寻觅着食物,只有死尸,她撕扯着,啃咬着,咀嚼
着。嘴里一股烧焦了的有机塑料的气味,她悲哀的发现这世界太干躁,枯萎
的竟然没有一滴血。
她饥饿着,舔噬着,哭嚎着,血,血,血……
来了,来了……一个声音颤抖着说。
她焦渴的喉咙被温热的液体充溢着。一个老人拿着一只空了的水杯呆坐在她
身旁,嘴里喃喃的说,菊苑,你醒了吗,你醒了吗,菊苑。
天黑着,世界里很静,静得没有一丝风。
这是一篇存在主义小说。
加缪说,人们越是爱,荒诞就越是牢固。
《饥饿》从此而来。
注:小说中灰和菊苑是精神统一体。
yulili1975
犀鸟文艺
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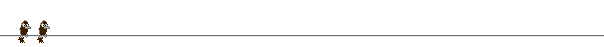 饥饿
饥饿